
张益唐,华人数学家,1955年出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在燕园度过7年时光,1985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教授。
从无限到有限的跨越
2016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北大78级经济系师兄田军来到位于中关村东路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拜访78级数学系校友张益唐。中科院数学研究所邀请他每年回国两个月讲学和做研究。
张益唐这个名字,在三年前尚不为人所知,如今,他是国际数学界的一颗明星,声名遐迩。
2013年4月17日,张益唐将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投给全球数学界最具声誉的《数学年刊》,在解决“孪生素数猜想”这一百年数论难题的道路上,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证明了在数字趋于无穷大的过程中,存在无穷多个之差小于7000万的素数对。
该论文被当今顶级的解析数论专家伊万尼克严格审核后,给予了如下评价:“这项研究是第一流的,作者成功证明了一个关于素数分布的里程碑式的定理”,论文在破纪录的超短三周内被《数学年刊》接受并很快得以发表。张益唐以新罕布什尔大学一个普通讲师身份,一鸣惊人,震惊了全球数学界。
张益唐教授位于中关村的这间办公室不大,一张书桌,一排书柜和一组简易三人沙发,简洁而朴素。续茶水的时候,张益唐会端着一个印有某次会议字样的白瓷杯,去楼道接开水。桌子上的演算本和稿纸,工整地写满了数字、符号和公式,显示出房间主人异于常人的意趣。

北大78级经济系校友田军与张益唐亲切交谈
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孪生素数猜想”开始。
“我研究过数学领域的很多问题,只是在孪生素数领域获得了成功。如果把数学这门学科分为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两大块,在理论数学中,很多尚未攻克的都是孤立的问题,它的解决不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是在研究中建立的方法论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张益唐教授告诉我们,孪生素数猜想由谁提出已经无从考证,一种说法是两千多年前,由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提出,在数学史上有据可查的是1849年。160多年来,对这个猜想的证实只到了函数级别,而这个函数是无穷大的。他的证明将函数变成了一个常数,也就是跨越了“从无限到有限”的巨大一步。
张益唐教授对“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发表后,其科学价值迅速得到体现。全球多位数学家开始运用论文中的方法,尝试突破7000万这个数值。
张益唐论文发表后的两个星期,这个常数下降到了6000万,在之后两个月内,又雪崩式优化到4200万、1300万、500万、40万,张益唐教授说,目前这个常数已达到令人吃惊的三位数,246。
同为北大数学系校友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汤涛,将张益唐教授的研究成果所起到的作用形象地比喻为:从“大海捞针”缩小到“泳池捞针”,未来极有可能“碗里捞针”。

从已经发表的对张益唐的采访文章中,我们了解了他博士毕业后七年的经历。因为种种原因,他无法获得继续攻读博士后、或者进入学术圈的机会。那段日子里,他以打零工为生,居无定所,辗转各州,游离于学术圈外,数学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直到1999年遇上两位北大数学系校友——唐朴祁和葛力明的帮助,张益唐才得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编外讲师的工作,由于教学出色,2005年成为该校正式讲师。
在新罕布什尔大学,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研究多年钟情的数学了。他平生的第二篇论文,关于“黎曼假设(也称黎曼猜想)”的研究,在这段时期发表在重量级的数学期刊《杜克数学》上。
他同时沉浸于“孪生素数猜想”,他说对数学难题的研究与最终的证明结果,往往只隔着一根头发丝的距离,而即使天分和运气都具备,跨越这样的距离,他也走了十三年漫长的岁月。
当我问到数学给他带来什么时,他微笑着说,“数学给我带来幸福,很难想象没有数学,我怎么过下去,现在还是这样!”
他用“清苦”概括自己研究数学的状况,却没有描述那些年生活的细节。他脑子里印象更深的是在音乐家朋友家度假,去院子里想看梅花鹿,梅花鹿没有出现,而灵感出现了的时刻。他说,“我知道我找到了方法,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刻!”那种豁然开朗,是数学给予他的激情和幸福。

我心里一直很平静
已过花甲之年的张益唐教授,身躯挺拔,头发乌黑,说话不紧不慢,浅蓝色衬衫上,挂着中科院数学院的胸卡,散发出温文尔雅的气质。他好像活在一个很干净的世界里,当下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环境,似乎没有污染到这片干净的世界。
他说,“我喜欢数学,这是个习惯,改不掉的”,“我按自己的习惯做下去,能不能出成果想得不多”,“我享受这样的过程”。
我调侃道,您那么繁重的脑力劳动,为什么不生白发不秃顶?他说数学对他来说不是苦事。
他从小在上海由外婆养大,八九岁的时候,买了《十万个为什么》的数学分册。他清晰地回忆起第八册是《数学》,第七册是《动物》,第六册是《地质地理》。他还记得第八册花了六毛五分钱,他对数学最有兴趣。而我则惊讶于他对数字的镌刻般记忆力。

本文作者83级经济系校友苏丹在采访张益唐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后来的中学数学知识是他自己找正规教科书学习的。不光数学,他阅读当时能找到的任何书籍,包括文学、历史、哲学。
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前,张益唐说他已经在《中国科学》杂志上读过陈景润的论文,那是1973年。虽然对于年少的他,“哥德巴赫猜想”很高深,但不知为什么,他能看懂一些,知道那是组合数学理论。
进入北大数学系,他是公认的高材生,很受后来担任北大校长的数学家丁石孙先生器重。张益唐心无旁骛,没有享受过未名湖的花前月下,他说,那时候人很单纯,只知道学习。
这两年,张益唐获得了一系列国际数学奖项,如美国数学会弗兰克·奈尔森·科尔数论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音乐学院、瑞典皇家艺术学院联合设立的罗夫·肖克奖;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等。当我问到他的获奖感受时,他说,“别人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还是跟以前一样。”“我的心里一直很平静。”
问到他理想中的生活,张益唐回答,“越简单越好”,但是他并非苦行僧。他爱白兰地、威士忌和葡萄酒,也喜欢喝茅台。他爱音乐,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推崇勃拉姆斯。

北大赋予了我家国情怀
张益唐多次表示北大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而且赋予了他敢于去挑战数学巅峰难题的勇气。他说,当时数学系的学生追逐菲尔兹奖,物理系的学生渴望诺贝尔奖,这是北大人才有的自信。
他很感谢导师潘承彪教授将他带进解析数论领域,潘教授培养的严谨学风,使他在日后的研究中受益匪浅。
顺着这个话题,我问他怎么看待老一辈数学家与七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数学家的区别,张益唐回答,纯粹的数学家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这一辈涉猎面和视野会更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当年陈景润用几麻袋稿纸来演算,后来才借助于一个袖珍计算器。现在的数学家可以用到人工智能,但是同样需要一个大脑和一支笔来演算。
两代人共同的地方是他们的家国情怀依旧,对科学的执着与追求不变,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家都一样。

按自己的方式定义成功
谈到成功,张益唐认为:成功的定义不是唯一,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按自己的定义获得了满足感、成就感便足矣。
虽然张益唐的同学们评价他是数学天分最高的人,但是他说自己当年在北大时并不是每次都能拿第一,用现在流行的词就是不应该被称作“学霸”。他想告诉学弟学妹们,当一个人出名后,媒体的过度吹捧是不可信的。人人都有弱点,学术和生活的道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所以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可丧失信心。
他曾用杜甫的两句诗来形容他的命运:“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他不过分关注名利,也没有来自家庭的压力。在这个方面,他说,我最感谢的是妻子Helen。两个人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不干涉对方,也不强求一致。Helen 不懂他的研究,但是曾经用朴素的语言表达过:“这个男人就这么点对数学的爱好,为什么要剥夺他呢?”
他觉得将“哥德巴赫猜想”当作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是一种文学上的比喻。数学领域的顶尖问题,无法简单地按难易程度排名,当你未得出结论的时候,所有问题的难度是一样的。攻克了“孪生素数猜想”对数学发展来说,与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都是非同寻常的大事。由于张益唐使用了新筛法,“孪生素数猜想”的进展,目前已经超过“哥德巴赫猜想”。
在张益唐心里,有110项研究成果的德国数学王子高斯、“费马猜想”的证明者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者佩雷尔曼都是他的标杆。在研究“孪生素数猜想”的同时,他还潜心于同样位列“七大数学世纪难题”之一的“黎曼假设”的研究。他不愿意拿出阶段性成果来发表,他要求自己出手就是“大东西”。张益唐说,如果“黎曼假设”得以证实,数学领域中将有上百个问题迎刃而解。

解读数学之美
在中科院附近的餐厅吃过晚饭,我陪张益唐再回办公室。穿行在物理所和数学所林立的大楼之间,我突发奇想,这样规规矩矩的大楼会不会禁锢一个科学家的思维?张益唐显然对国内的情况颇有洞察,用一个提问来回答我,盖这些楼是因为研究经费需要花完吧?
他的研究方式似乎不是在书桌前苦思冥想,我随意问起他的作息时间,他的回答不禁令人莞尔。他作息规律,早睡早起,起床前在床上想一会儿数学问题,似乎折磨我们的数学对他来说是放松。
张益唐坎坷的学术之路和曲折的人生,在过去的三年中已经有了许多的解读。乐于中国式皆大欢喜结局的人,欣慰地看到他现在功成名就,认为是对“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极佳诠释。
对这位曾经的隐士更深入地发掘,会发现他让中国的学术界看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类型:游离于主流的数学界,成名前只发表过两篇论文,不在乎名气和物质,醉心于自己的爱好,最后一鸣惊人。在采访中,我所看到的是一个热爱数学,充满自信,脱离世俗的科学家。
这位享誉盛名后的数学家对未来怎么考虑呢? 当我回来反复听采访录音时,深深打动我的,是张益唐说的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我还能继续做事情,数学领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那些问题都非常难又非常重要,我尝试过很多种,有一些取得了部分结果。至于其它的,我没想那么多,我不喜欢出了名之后捞好处,我没那么想过,也不会那么去干”。
我注意到他反复说到数学之美,起初十分难以理解。当我追问,是不是如同音乐具有旋律之美,建筑具有均衡之美一样?他表示赞同。法国几何学家E.cartan说:“在听数学大师演说数学时,我感觉到一片平静和纯真的喜悦。这种感觉大概就如贝多芬在作曲时,让音乐从他灵魂深处表现出来一样。”从张益唐学长身上,我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
我还感受到了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如同勃拉姆斯始终坚持古典主义形式创作音乐,因为没有达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水准,而迟迟不肯发表自己的《第一交响曲》一样。在张益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平静的状态背后,隐藏着某种理想,隐藏着一种通过追求学术巅峰,不负燕园、不负家国的内心世界。

“若有所思”似乎是张益唐的经典表情
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中,第四乐章是以“欢乐颂”的旋律,向“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致敬的经典篇章。如果按照传统交响曲快板—慢板—小步舞曲—快板的结构,把张益唐的人生经历写成一部音乐作品,我想,第一乐章如歌的行板,是燕园时光和在美国的普渡岁月;第二乐章:七年颠沛和十三年孤寂的学术生涯,犹如低沉的慢板;第三乐章:“孪生素数猜想的证实”及国际上的巨大反响,是快乐的小步舞曲;未来的第四乐章,也许是张益唐向数学大师致敬的华美篇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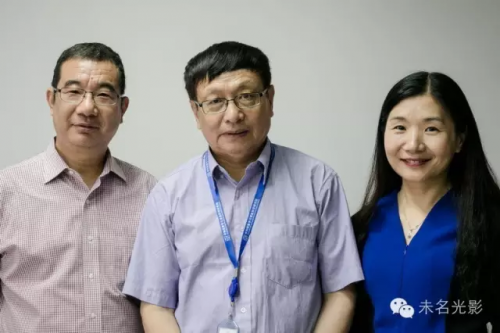
采访结束后,田军、苏丹与张益唐合影留念